我们先梳理一下李朝阳债权债务的产生过程及其相互关系。 首先,李从村委会手中接手了这个项目。 然后分包给赵毅。 (赵毅垫付了工程款,因此李某欠赵毅工程款。)其次,赵毅将工程分包给了杨兵。 (所以赵某欠杨某工程款)接下来,杨某要求赵某垫付6万元。 赵要求李来先付款(因为李来欠赵的工程款)。 于是李预付了6万元(但是以借条的形式)。 欠条在李手里。
上述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任何疑问。
2、本案中,杨兵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被告之一李某并未以欠条要求杨兵还款。 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
胡文说:本案中,“应该说,李佳用杨兵借的6万元还清了欠赵B的工程款。这是李佳和赵B双方都承认的事实。当赵B B与杨冰和解,欠条上有写。” “杨兵本人收到6万元”这一事实是有证据证明的事实。 这两个事实都具有基本事实的可靠性特征。”
鉴于本案中李某并未以欠条向杨某还款,这一事实说明“李甲用杨兵借的6万元还清了欠赵毅的工程款”,这一事实是公认的。李嘉和赵毅都写的”,这是真的。 。 这6万元是用来还清欠赵毅的工程款的。 由此可见,赵某在2008年1月之前已向杨某支付了6万元。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欠条、李佳、赵毅的认可)确定,毫无疑问。
3、本案有哪些证据? 其特点是什么?
本案有多份书证和当事人的口头陈述。 书面证据包括(一)借条; (二)证书; (3)欠条。 另外,还有当事人(李朝阳)的口头陈述。
上述三个证据事实有何特点? 仅看这三个书面证据本身(如果它们之间没有联系的话),它们具有以下特征:(1)欠条(发生在李佳和杨兵之间,没有赵毅参与。杨向李借了钱6万元,并开具欠条,存于李某手中。) (2)证明(发生在赵毅与李佳之间,无杨兵参与。) 欠条(发生在赵毅与杨兵之间,无李佳参与)。
4、“杨兵本人已收受6万元”欠条的问题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2008年3月20日,在开具借条两个月后,赵某向杨某开具了借条。 欠条称:“今日,杨兵共欠修路工资1万元,杨兵本人已收到6万元,欠款8.85万元。”
不仅如此,杨兵在法庭口头陈述中称,“欠条上的‘杨兵本人已收到6万元’字样,是他向李佳借的6万元的扣除额。” 杨某承认,这6万元是原来扣除的(向李某借的)。 杨某的口头陈述与欠条记录是否存在矛盾? 不会,也算是对欠条记录的一个合理解释。
另一方面,赵毅的说法也前后矛盾。 胡文表示,庭审中,李佳和赵毅均承认,在和解过程中,他们已将杨兵向李佳借的6万元记入李佳应付赵毅的工程款。 杨冰开的欠条并没有交给赵毅。
这意味着杨某的取款行为会产生以下两个后果。 一是冲销账户。 李佳实际上向赵某支付了该项目6万元的费用。 如果李某之前欠赵某6万元的工程款,杨某拿走李某的6万元后,李某就不会欠一分钱的零钱。 李某、赵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已解决。 (证明上记录了这一事实。) 其次,既然杨某拿走了李某的6万元,就意味着赵某已经向杨某支付了6万元。 如果赵某在该项目上总共欠杨某10万元,那么扣除这6万元后,他还欠杨某4万元。 那就是我的意思。
然而,“赵毅声称,给杨兵开的欠条并没有扣除杨兵向李佳借的6万元,所以他只欠杨兵28500元的工程款。”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不能用前面所说的来证明其合理性。 明明是扣了,为什么说没有扣呢?
5、杨冰是否有必要收回欠条?
不会。因为,第一,李兆军承认(当事人的陈述)是支付赵毅的工程款。 其次,李某与赵某之间有一份证明(证明文件)。 胡文称,2008年1月,李佳与赵毅办理了和解手续后,赵毅出具了一份证明,上面写着:“我与李佳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结清,特此证明。” 第三,李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李佳和赵毅均承认,在结算过程中,他们将杨兵向李佳借的6万元抵扣为李佳应付赵毅的工程款。 (这6万元是李某欠赵某的工程款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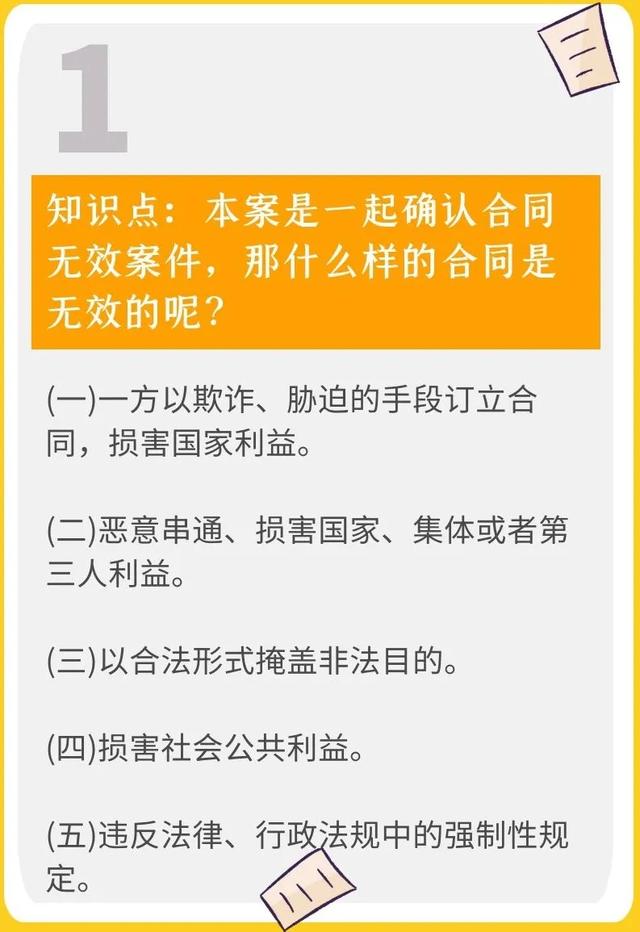
以上三项证据构成了一条严密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杨某并不欠李某任何钱财。 因为这6万元是杨(赵)应得的工程款的一部分。 由于李某欠赵某钱,赵某要求李某代其还钱。
6、如何理解胡文关于“双方均无书面证据证实”的说法?
胡文表示,“双方都没有书面证据证实”。 需要确认什么? 这应该如何理解呢? 我们知道,“杨兵本人已收到6万元”是赵毅给杨兵开具的欠条中的一句话。 对于欠条上的这一事实,胡文表示,“双方均无书面证据证实”。 为什么我们需要书面证据来证明? 为什么不允许口头陈述? 胡文没有给出理由。
原告杨兵在法庭口头陈述中称,“欠条上注明的‘杨兵本人已收到6万元’字样,是他向李佳借的6万元所扣除的。这是当事人之一(杨兵)的认可”。是一种强有力的证据。
但被告赵毅不同意原告的说法,遂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未被法院采纳。 (胡文介绍,“在上述案件中,赵毅曾申请与杨兵和解时在场的证人出庭作证,证明赵毅与杨兵结算劳动工资后,赵毅退还了工资”)法庭在鉴定证据的过程中,认为证人陈述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证人没有参与整个和解过程,所以它不接受证据。”)
由上可见,原告和被告均对欠条中“杨兵本人收受6万元”的问题有证据,但被告证据薄弱,被法官排除。 原告的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符合推定的适用条件。 应用举证责任规则的唯一方法是拒绝被告的证据并接受原告的证据。 可见,法官在欠条问题上并未采用推定方法。 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 胡文说:“本案中,法院认定赵毅开具的欠条中扣除的6万元与杨兵向李佳借的6万元为同一数额,是通过推定认定的。” 这是一个误解。
如果双方都没有证据证明欠条中“杨兵本人收受了6万元”的问题,则可以采用推定方法来推定一个事实(推定事实)存在。 但本案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三)关于基本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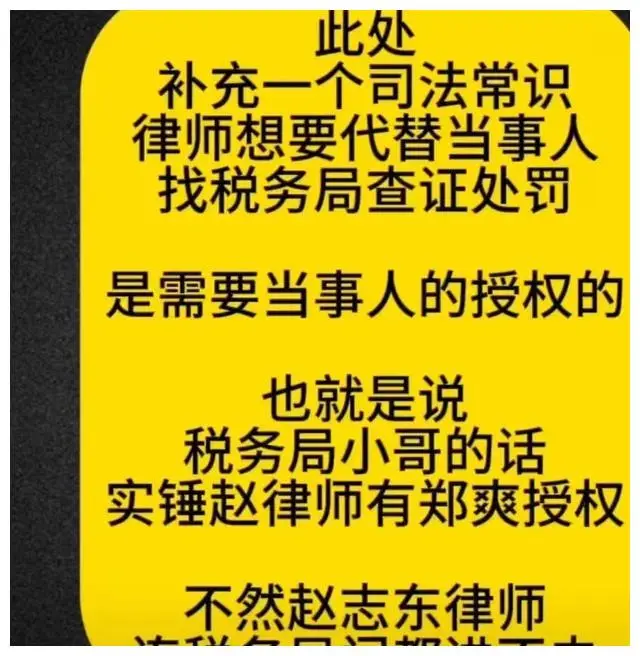
在上述案件中,胡文指出:“法院认为,杨兵向李嘉偿还的贷款不是小数。赵毅声称,他在计算总账时忽略了金额,不符合通常的行为。”这种推定将行为逻辑模型的概念强加给赵毅,这对赵毅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推定,因为杨兵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他和结算时,赵毅已经还清了该项目的债务,如果欠条无法收回,则应在欠条上注明收到的6万元已用于抵偿债务,这样,即使李佳使用了欠条今后再次向其索要款项,仍可以向其索要款项。赵毅对此案进行了追究,故推定事实与本案基本事实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不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可能。”
从上面可以看出,胡文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基本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应当存在必然联系; 其次,这种联系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1、基本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毫无疑问,潜在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本质是什么? 是必然的联系,可能的联系,还是其他的联系? 这需要仔细分析。
《加州证据法》第600条规定,推定是基于另一个事实或多个事实之和的证明力而假设一个事实存在。 根据该规定,所谓推定事实是指“推定事实”。 它并不是像严格的逻辑推理那样具有必然联系的结果。 也就是说,基本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联系,而是一种可能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正因为如此,在推定事实作出时,不受益的当事人如果发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就可以反驳、推翻推定事实。 因此,笔者这里所说的“必然联系”是不准确的。
如果基本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只有“必然联系”(唯一正确答案),那么推定的适用范围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2. 基本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否应该具有“高概率”?
按照胡文的本义,基本事实不等于推定事实。 这是常识。 概率就是可能性。 胡文认为,基本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应该具有“高度的概率”。 作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基本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不存在高度可能性。 哪怕有可能,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也是允许的。 以推定死亡为例,死亡事实与推定死亡之间的联系并不一定需要“高概率”。 因为假定的事实就是假定的事实。 从基本事实到推定事实,有时可能性很大,有时只有(推定)可能性而不是高(或高)可能性。 因此,使用“高概率”作为本案适用推定的条件可能并不合适。







